Advertisements

一詩一會 · 113

查爾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1920—1994),美國當代先鋒詩人,散文家、小說家。
從13歲起,查爾斯·布考斯基便接觸到了平生兩大嗜好:寫作與喝酒。作為一位異常多產的作家,他一生寫了五千多首詩,出版有六部小說集、數百篇短篇故事,但直至50歲左右才真正名聲大噪。阿爾貝·加繆稱他為美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時代周刊》將其譽為“美國底層的桂冠詩人”。
由于布考斯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洛杉磯,他的作品受洛杉磯的社會環境影響很大。他擅長書寫美國社會邊緣窮苦人民的生活,無業游民、酒鬼和妓女都是他故事里最常出現的主人公。布考斯基本人同樣窮困潦倒,唯有酒、女人、賽馬和古典音樂不可或缺。為了謀生,他從事過五花八門的工作,諸如洗碗工、卡車司機、郵遞員、門衛、加油站服務員、倉庫管理員、電梯操作員等,與此同時,他也將生活中的卑微、骯臟,荒謬乃至瘋狂,都酣暢淋漓地寫入作品中。
1965年,當時還是辦公用品經銷商的約翰·馬丁在一份地下刊物上看到了布考斯基的作品,他立刻意識到自己挖到了寶。他首先給布考斯基寫信建立聯系,并于次年成立了黑雀出版社(Black Sparrow Press),以供布考斯基全職寫作。作為粉絲、摯友和文學經紀人,約翰·馬丁在布考斯基人生最后的20多年間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成功地將一個地下作家推到了文學圈的聚光燈下。
然而,布考斯基的成功絕不是由于一時的幸運。盡管他35歲時才開始創作第一首詩,還曾數次被雜志社、出版社退稿,但在寫作這件苦差事上,他比絕大多數人更勤奮、執著,也更甘之如飴。正如他在寫給約翰·馬丁的一封信中所言:“沒有什么能比在紙上寫出一行行句子,更有魔力、更美好。全部的美都在這里了。一切都在這里。任何獎賞也都沒有寫作本身更偉大,隨之而來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近日,布考斯基的書信集《關于寫作》中文版出版,收錄了布考斯基寫給出版人、編輯、朋友和作家同行們的近150封信。就大部分內容而言,這些書信都有明顯的即時性,布考斯基很少說套話,總是在信中侃侃而談,以滿腔熱情討論著日常事件,坦率地分享他的創作洞見。對他而言,寫作類似一種無藥可救的愉快的疾病,而詩歌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他從始至終堅持創作一種清晰明了、從生活出發的詩歌,反復批評那些公認的偉大作家,認為他們的創作都是陳詞濫調、空洞無物。在這些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布考斯基最典型的特質:生猛、機智、動人、干脆利落、毫不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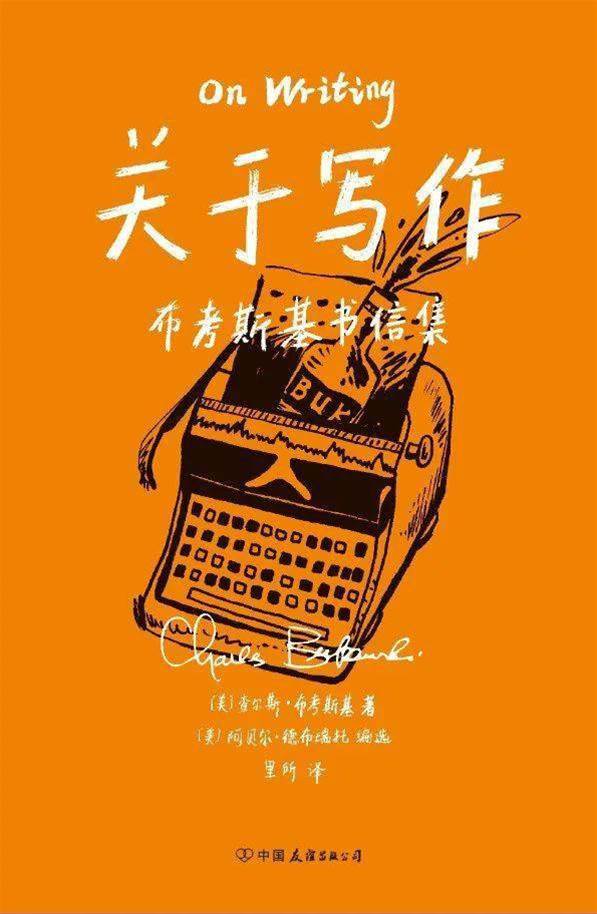
《關于寫作:布考斯基書信集》
[美]查爾斯·布考斯基 著 里所 譯
磨鐵圖書 |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21-04
致喬恩·韋伯 ( 1961年1月底)
……當你為了要“作”一首詩而在詩中對自己說謊的時候,你就失敗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從來不會反復修改自己的詩,而是保留它們最初被寫下的樣子,因為如果我從一開始就說謊,再怎么修改都救不回來,如果我沒有說謊,嘿,那就沒有什么可擔心的。有時我讀一些詩,總能察覺到它們是怎樣被修剪、打磨、固定在一起的。你可以在現在的芝加哥《詩歌》上看到很多這樣的詩。當你翻閱那一頁頁紙,空無一物,除了花拳繡腿,幾乎都是沒有生命的蛾子在亂飛。當我翻看這本雜志時,我真是被嚇到了,因為那里面什么都沒有。我猜這就是他們所以為的詩歌的樣子,好像詩歌就應該是空無一物的東西。就是些精致分行排列的東西,太精致了以至于我幾乎都感覺不到它的存在。詩歌完全被變成了智力藝術。滾去吧!唯一能體現一件好藝術品有智力的地方在于,它能讓你被活生生地觸動,否則就都是胡扯,你告訴我,芝加哥《詩歌》上怎么會有這么多瞎胡扯的東西?
我第一次開始寫詩是在1956年,當時我35歲,在長時間的上吐下瀉之后,我已蒼老無比,我確實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喝那么多威士忌了,因為有個女士聲稱我上周五晚上喝著波特酒在她那里蹣跚地走來走去——1956年我給《實驗》寄去了一些詩,他們當時接受了,現在過了五年之后,他們告訴我說他們要發表其中的一首詩,他們的反應可真夠慢的,但好歹終于有了回復。他們告訴我那首詩會于1961年7月被刊登出來,我想當我讀到它的時候,會像是在讀自己的墓志銘吧。然后她建議我匯給她10美金,這樣就能加入他們的《實驗》了,自然,我拒絕了。天哪!要是能在今天的中距離賽馬中,我再押上10美金在“團結”(賽馬的名字)身上,那可夠我再爽一陣子的……
致喬恩·韋伯 (1962年10月底)
布考斯基被《局外人》的編輯評選為“年度局外人”,菲利克斯·斯蒂芬尼爾在一封信里發表了對此事的看法。下面這封信則是布考斯基在對菲利克斯·斯蒂芬尼爾的回應。
……關于斯蒂芬尼爾:像菲利克斯這樣的人應該經常什么都搞不明白。至于詩歌應該是什么樣子,他們有很多概念和前概念,多半他們還停留在19世紀。如果一首詩看上去不像拜倫勛爵那種調調,那你就只是寫了一堆如床上的餅干屑般破碎的文字而已。政治家們和各個報紙大談特談著關于自由的言論,可一旦你真的試圖得到自由——不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藝術形式上——你卻被關進了牢房,面對著嘲諷和誤解。有時當我把一張白紙放進打字機里,我常想……你很快會死去,我們都會很快死去的。這么說死去可能不是什么太壞的事,但既然你還活著,你最好按照深藏你內部的秉性活著。可要是你足夠誠實,你可能早已在醉漢監禁室了結過15或20次啦,你可能失去了幾份工作、一兩個老婆,你可能在街上把某個人重擊在地,時不時地只能睡在公園的長椅上。要是你開始寫詩,你無須擔心自己寫得像不像濟慈、斯溫伯思、雪萊,你也不用像弗羅斯特那般行事。你不用擔心揚揚格、字數和結尾要不要押韻。你只想寫下它,猛烈地,粗魯地或用其他方式——任何你能真正寫出自己的方式。我可不認為這意味著我“在左外場尋歡作樂”……扯著我最大的嗓門,“舞動著雙手在表演”,我可沒有像斯蒂芬尼爾先生提到的那樣,“揮舞著他的詩像揮舞一面旗子”。由此可以推斷有些人不惜任何代價地想獲得廣為人知的感覺;由此可以推斷壞藝術只是為了追逐名聲;由此可以推斷有些人是在表演和招搖撞騙。不過這些罪名在所有的藝術領域早已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并且它們現在繼續在繪畫、音樂、雕塑和小說領域肆虐。大眾,普通大眾和藝術大眾(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僅僅是些練習生)永遠都是滯后的,不論是在物質和經濟生活方面,還是在所謂的精神生活方面,他們總想過得安全一點。假如你在12月戴著一頂草帽,你就蠢死了。假如你寫的詩脫離了19世紀那種老套柔軟的韻詩的巨大催眠術,他們就會認為你寫得差極了,僅僅因為你的詩聽起來就不對。他們只愿意聽見他們經常聽見的東西,但是他們忘了,每個世紀里,都會有五六個非凡的人物要把藝術和文學從陳腐和死亡之中拽出來,再把它們向前推進。我并不是說我就位列那五六個人之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會屬于他們之外的其他人群。正因如此,我被懸身局外。
好吧,喬恩,我想說如果你找到版面,就把斯蒂芬尼爾說的那些話發出來,那也是種觀點。我倒寧愿被描述成一個砌磚匠或拳擊手,而不是一個詩人。所以這一切也沒什么不好的。
致威廉·帕卡德 (1972年10月13日)
關于詩歌寫作,我們還是應該玩得輕松點。很高興我還能寫點散文,還能喝酒,還能為了終止痛苦而和女人做斗爭。我接受了一些關于詩歌技藝的采訪,我感覺那些人都是被打磨好的紅木。我猜那是因為他們學習得太多而生活得太少。海明威用力在生活,但他后來也被鎖在了技藝里,很快技藝就變成了他的牢籠并殺死了他。我猜測這大約都是我們怎么選擇自己道路的問題,這都是當我們還是孩子時迷失在一處碼頭上的寫照。迷失是很容易的,迷失。當然我也并非要站在什么制高點上說這些。讓我們為幸運喝一杯,同時懷揣著女人們依然會愛我們衰老靈魂和干枯大腿的希望。哦,如何寫詩,該死!
附上更多我的詩。我正試著建造一個詩庫,我要用我的詩歌炸毀這個世界。是的!

布考斯基所繪的自畫像
致威廉·帕卡德 (1984年5月19日)
好的,既然你問了……否則,討論詩歌或缺少了詩歌會怎么樣,真的有點太過“酸葡萄”——關于水果不好吃的老套表達。這真是蹩腳的開場白,不過我只喝了一口酒。老尼采看得很準,當他們問他(也是發生在過去的事了)關于詩人的問題,“詩人?”他說,“詩人們說了太多謊話。”這只是他們所有錯誤中的一個,假如我們想知道詩人們到底怎么了或現代詩歌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也需要回頭看看過去。你知道,現在學校里的男孩們都不喜歡讀詩,甚至還要取笑詩歌,將詩歌看低為某種娘娘腔的運動,他們這是徹底錯了。當然這里面有一種長期積累的語義學轉變,使得讀者很難全神貫注地去讀詩,但這還不是讓男孩們放棄詩歌的最主要原因。詩歌本身就出了問題,它是假的,它沒法觸動任何人。拿莎士比亞舉例:讀他的東西簡直令你抓狂。他只是偶爾能點中要害,他給你一個閃亮的鏡頭,然后又回到不痛不癢的狀態直到下一個要害出現。他們喂給我們的詩人都很不朽,但他們既沒有危險性也不好玩,我們就會把他們丟到一邊,去找些更正經的事情做:放學后打架打到鼻子流血。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你不能盡早進入年輕人的意識里,最終你只能見鬼去吧。愛國者和信仰上帝的人都非常明白這一點。詩歌從來都沒有做到過這一點,并且看起來未來依然做不到。是的,是,我知道,李白和別的一些中國古代的詩人可以只用幾行簡單的句子,就表達出一種偉大的情緒和偉大的真實。當然,也有例外,盡管還沒能跨越更多的階梯,人類也并非一直都是殘廢的。但大量的紙書印刷品和與之相關的東西都非常不可靠,都空洞無比,幾乎都像某個家伙對我們做的惡作劇,或者比這還要糟糕:很多圖書館都是笑話。
現代借鑒過去,并延續了過去的錯誤。有人聲稱詩歌是寫給少數人的,不是給大眾看的。很多政府機構也是這樣,還有那些富人、某個階層的太太們,還有那些特別建蓋的廁所。
最好的研讀詩歌的方式是閱讀它們然后忘記它們。如果一首詩無法被讀懂,那我不會認為它有什么特別的可取之處。很多詩人都在寫一種被保護起來的生活,他們可寫的東西非常有限。比起和詩人們聊天,我經常更愿意和清潔工、水管工或炸點心的廚師聊天,因為他們懂得更多關于生活的日常問題和日常歡樂。
詩歌可以是令人愉快的,詩歌可以寫得清晰明了,我不理解為什么它非得被弄成別的樣子,但它確實就成了那種樣子。詩歌就像坐在一間悶熱的、窗戶關死的房間里,任何空氣和光線透進來的可能都很少。很可能這個領域已經被從業者徹底敗壞了。每個人都太容易把自己稱作“詩人”。當你假定了自己的立場,你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大多數人不讀詩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現有的詩都太差、太無力。難道精力充沛的創造者都去搞音樂、散文、繪畫或雕塑了嗎?至少在這些領域里時不時還有人能推翻陳腐的高墻……
致A.D.維南斯 (1984年6月27日)
……我想對我來說最幸運的事情是成了一個作家。50歲之前我一直都不成功,不得不四處謀生。這讓我得以遠離其他作家和他們的社交游戲,并且遠離他們的中傷和抱怨,既然現在我已經有了一些運氣,我依然會讓自己離他們遠一點。
他們繼續他們的攻擊好了,我只想繼續我的寫作。我這么做也不是為了尋求不朽或什么名聲。我這么做因為我必須去寫和我想寫。大部分時間,我感覺都挺好的,特別是每當我坐在這臺機器前,詞語不停涌出,并且好像語感真的越來越好了。不管這是真是假,不管這么做是對或錯,我會一直寫下去。
致亨利·休斯 (1990年9月13日)
1990年1月,亨利·休斯在《梧桐評論》上發表了布考斯基的詩。
很高興我有幾首詩被你選中了。
我現在70歲了,只要紅酒還在流,打字機還在響,就都沒問題。當我為了房租給那些男性雜志寫黃色故事時,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場精彩的秀,現在它依然很精彩——我邊寫作邊對抗著各種蠅頭小利的危害,對抗著“終結”這個標牌鄰近的腳步。有時我很享受這種和生活的辯論,換句話說,離開時我也將毫無遺憾。
有時我把寫作稱為一種疾病。如果真是這樣,我很開心這種病找上了我。每當走進這個房間,看著這臺打字機,我總能感覺到某些來自別處的事物,某些奇異的神靈,某種完全難以形容的事情,正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絮絮叨叨的、絕妙的幸運觸動著我,并且這幸運的感覺在持續、持續、持續。哦,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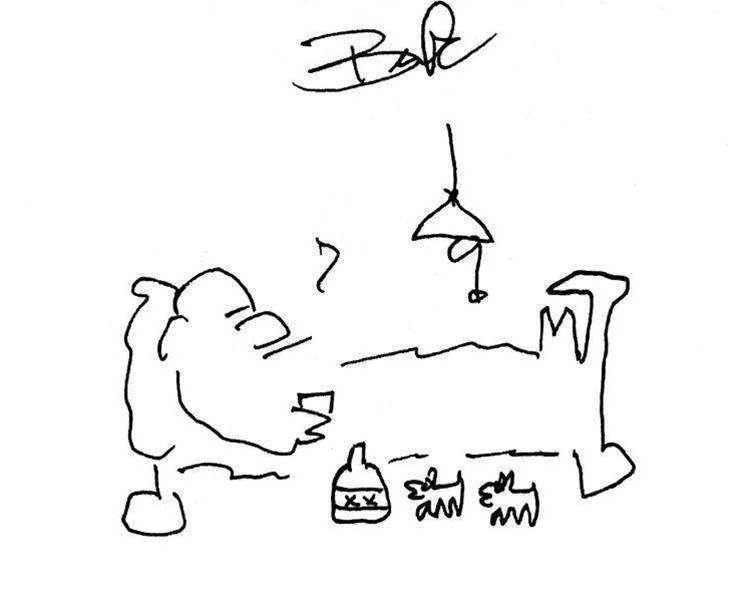
在《致亨利·休斯》這封信的末尾,布考斯基附上了一張小畫。
本文書摘部分選 自 《關于寫作:布考斯基書信集》 一書 ,較原文有刪減,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按語寫作/編輯:陳佳靖 ,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