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s
米沃什的回憶錄《歐洲故土》有個副標題“對自我界定的探求”,事實上這個副標題也適用于他的詩歌。就此而言,把詩歌視為自傳固然不錯,但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寫詩是認識自我的過程。正如希尼在《個人的詩泉》中所寫的,“我作詩是為了看清自己”,詩人在他編織的詞語中呈現自己或辨識自己,有些詩歌中的自我形象很清晰,有些卻比較模糊,這不僅是表達功力問題,也和詩人對自身的認識不夠或不準有關。
因此,寫作是用詞語回答“我是誰”或“認識你自己”的一種方式,而寫作中的靈感則是詩人在某種特殊處境中用詞語迅捷而準確地呈現自我的激越狀態。這時,詩人筆下的詞語對詩人自身的形象完全敞開,而在慣常時刻,詩人自身的形象對詞語是全封閉或半封閉的。事實上,詩人形象對詞語的全封閉或半封閉狀態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一個詩人會在詩中完全袒露自己嗎?未必。詩人的每次抒情其實都有一個特定的傾訴對象,如果傾訴的對象足夠親密,他就會不自覺地袒露自己,而在更多情況下,詩人都有所保留,可以說隱藏自己是存在于詩人心中的頑固傾向,它接近于一種本能,和自尊與自我保護有關。

宋琳,1983年畢業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現居大理。著有詩集《城市人》(合集)《門廳》《雪夜訪戴》《口信》《宋琳詩選》《星期天的麻雀》(中英)等。
1
說這些并不意味著我把自我呈現的清晰度作為評判一位詩人成就的唯一標準,但把它作為一個觀察點還是很有意義的。我是讀了《兀鷹飛過城市》想到這個問題的,因為這部詩選至少從四個方面呈現了詩人的自我形象:空間、時代、歷史上的他者與現實中的他者。該書是作者用生活過的城市編排的: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諾斯艾利斯,北京,大理。《在紐約上州鄉間的一次散步》表明還有在美國的游歷,從這個空間變換至少可以看出兩點:國際視野和漂泊經驗,它們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宋琳的詩歌,并促成了宋琳詩歌內部的張力:國際視野當然拓展了詩人原本狹隘的本土眼光,而異域漂泊卻增強了詩人強烈的歸宿感和漢語鄉愁,尤其是后者構成了宋琳詩歌的核心因子。
《火車站哀歌》《閩江歸客》《斷片與驪歌》堪稱其漂泊三部曲,分別書寫了漂泊、還鄉和異域生活。如今他已回歸大理,深入云南大地,沉浸于漢語典籍,這是一個沒有異域漂泊經驗的當代詩人難以企及的。事實上這也是他的詩友張棗,以及上一代詩人北島、多多共同的文化路向:曾經滄海,終歸本土。這批當代歸來者詩人往往比本土詩人更親近古代漢語,將古代漢語視為終極的精神家園,在詩中呈現出鮮明的古典傾向。其中,《雪夜訪戴》《廣陵散》《阮籍來信》應是宋琳此類作品的代表作,因為他與寫作對象性情契合,寫歷史人物也寫出了自己,都屬于散漫不羈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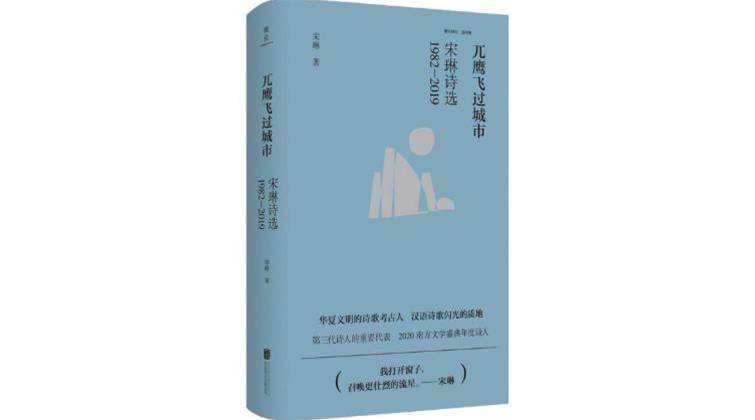
《兀鷹飛過城市》,作者:宋琳,版本:雅眾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2
我更看重宋琳對現實中的他者的書寫。與那些一味自戀的詩人不同,宋琳非常關注同代人(也包括同代詩人),尤其是身邊的人甚至是偶然遇到的人,并以深情或同情的筆觸寫到他們。《阿怒日美》是我特別喜歡的篇章,其中寫到溜索人、洗發女子,以及《火塘》中的一家人,這些作品都能顯示宋琳作為一個畫家的功力:細膩傳神,充滿動感,多維交織,彼此輻射,精彩地呈現了特定地方和風俗中的人。
這首《沙溪口占》讓我暗暗喝彩,這個鮮艷的農婦肯定也曾經讓作者喝彩。如果說“不受任何東西差遣”的流沙體現了詩人的自由情懷,掰苞谷的農婦則令我感動:詩人看到了她的鮮艷,更感到了她的辛苦,“每一滴汗都匯入了下游”,將人事融入自然,可謂至高的贊美。客居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宋琳寫過一首《契多街》,一個每天坐公交車的老婦人總是“把黑頭巾從頭上取下,戴上,又取下”,而“我敲打鍵盤,停頓,繼續敲打。”于是,詩人看到了自己和一個陌生人的相似處境與共同命運:“在這相似的動作里,我們重復著/同一種虛無,同一種瑣碎,/仿佛兩個溺水的人,朝向對方打手勢,/直到水涌上來,淹沒了頭頂。”寫這些陌生人時,宋琳顯然是敞開自己的,但對方并不能看到。所以這只是單向的敞開。一般只有在親友之間才能形成雙向的敞開。宋琳的親情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寫給長兄和同學的,如《書簡片段》《二十年后》,這些詩應該是宋琳詩中最抒情的,而抒情強度與詩人內心的敞開程度是一致的。
3
宋琳的精神肖像在《三十五歲自題小像》中得到了集中的表達。“眉宇間透出白日夢者的柔和”,“因見識過苦難而常含寬恕”,這是他對自身形象的精準把握。
宋琳確實是個柔和溫潤的人,但這只是他形象的一面,另一面是“面頰的陰影燃燒著南方人的熱情”,對時代與寫作的雙重熱情:“鼻梁正直”“額頭不曾向權勢低垂”“這張嘴化為塵土以前將把詩句沉吟”。就此而言,宋琳是外柔內剛,剛柔相濟的詩人。此外便是愛美與好奇:“在美的面前,喜歡微微瞇起”,“我對宇宙充滿了好奇”(《我見識過一些城市》)。值得注意的是,《痛苦的授權》對其精神肖像有重要的補充:
由此來看,關于父親的應寫之詩之所以仍是未寫之詩,詩人把原因歸結為“害羞和離奇的懶散”,懶散或許屬實,但理由并不強大,因為他畢竟已經寫了許多作品。在寫與不寫之間,詩人其實做了無意識的取舍。這樣說來,“害羞”便顯得更重要了。它決定著一首詩的寫與不寫,也決定著一首詩的敞開度與隱藏度。
事實上,害羞絕非宋琳獨有,而是許多詩人的共性。詩人的羞澀通常并非由于詩人對自身寫作技藝的疑慮,而是隱藏自我的一種傾向,而這通常和特殊題材有關,可能涉及道德感或其他,也就是說,羞澀大多是寫作者面對不宜公開的題材的普遍傾向。其中既有前述的自尊因素,也有追求藝術真實性而在當代語境中暫時不可能做到之間的張力。
4
宋琳還是一個能直面現實的詩人,他曾這樣質問:“告訴我,在公眾事件中始終不吭一聲的同行,/是否從被拋棄的芻狗那里贖回了本屬于你的悲憫?”(《雙行體》)
作為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宋琳的寫作觀也是其時代觀的一部分。他的不少詩具有張棗所說的元詩意味,尤其是《詩話三章》直接表達了他的詩觀:“詩,緣情而發/遇事而作,不超出情理/把哀怨化為適度的嘲諷/用言說觸及不可言說者/理念完成于形式的尺度。”在《厭倦了挽歌》中,宋琳對當代詩音樂性的匱乏提出了批評:“……我們時代的大多數詩歌,/誰都能玩,但難以形成音樂。/人們爭論不休,陶醉于口語/或非口語的胡鬧……”在《內在的人》中,宋琳將詩人的角色定位成“回聲采集者”,也表明了他對詩歌聲音的重視。宋琳的詩歌整體上比較精致,但他并非一個詩歌的形式主義者,他清醒地意識到:“語言,詩人所依賴的,如果在運作中不能觸及被稱為邊界或深度的東西,即使徒有形式,也難以留存。”就此而言,宋琳的詩歌可以概括為深度情思與精致聲音的融合。
總之,《兀鷹飛過城市》這部詩集呈現的自我形象或精神肖像復雜深邃,是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在流動多維的處境中呈現自己、同時呈現一個豐富世界的優美晶體。
撰文|程一身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寧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