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s
1991年9月,在北京西郊的萬泉河,發現了一具年僅24歲的尸體。
他身上背著一整包的石子,能將人完全沉沒在河底。
后來又在公廁里發現了被丟棄的一個書包,里面正是死者生前全部的詩稿作品。
由于在污水里浸泡太久,打撈上來的時候,很多字跡都變得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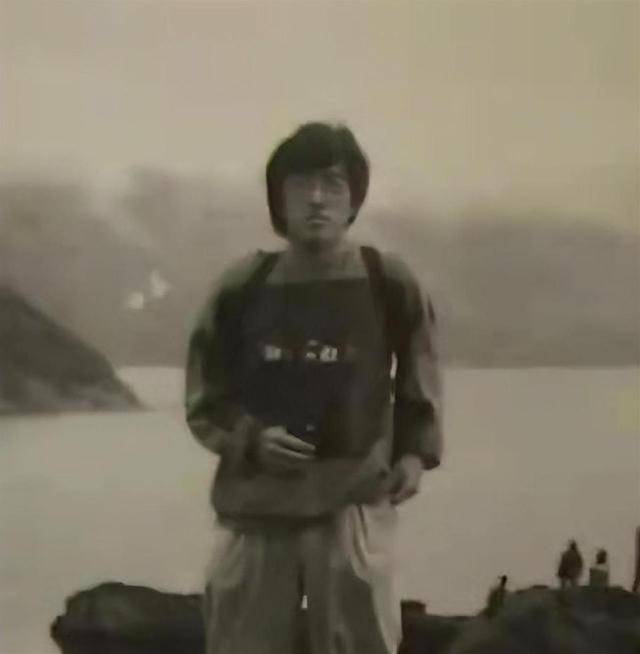
這時候人們才發現,死去的是北大詩人戈麥。
在場的人都說,他不僅對自己的作品格外厭惡,恐怕也沒有任何求生的欲望了。
那么他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才選擇在大好的年華自殺?
對于戈麥自殺的原因,很多人都做出過一些猜測:
有人說是因為他從小非常敬重的母親突然去世了,這件事對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有人說戈麥曾跟看相術的老人來往甚密,很有可能是被“洗腦”了。
雖然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放在生性敏感、而且還帶有“宿命傾向”的戈麥身上來說,仿佛又有些說得通。
還有人說“戈麥”這個筆名就取得不吉利,帶有一些殺戮的意味,恐怕結局也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
但這種頗帶迷信的說法經不起任何的推敲。
其實他的死因,就藏在被丟棄于廁所的“過往”之中。
2
他出生于三江平原的曠野之上,也是黑龍江建設兵團下屬的農場,就是人們所熟悉的“北大荒”。
在家里的五個孩子之中,他排行老幺,更是被起了一個飽含家人疼惜的名字----褚福軍。
或許是那里荒涼、孤僻的土地具有神奇的色彩,讓戈麥自小就有了一種獨特的氣質。
與他之后所顯現出來對于文學的靈性以及天賦,應該也不無關系。
再加上大他20歲的哥哥熱愛文藝,每當看到哥哥讀書、畫畫都會讓年幼的戈麥產生一種好奇的情緒。
那個年代沒有電子產品、也沒有網絡,更多的就是日復一日的勞作,讀書好像就變成了唯一的精神食糧。
這讓戈麥的成績在上學之后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他不出所料的選擇了文科。
就當人們歡呼于18歲的戈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后,他卻動了想要復讀重考的念頭。
此時戈麥的“極端性”就有些端倪了。

盡管很喜歡文學,但在高考前夕接觸到了“經世濟民”的思想后,成為了一名實用主義者。
他“狹隘”的認為,只有創造出什么,才能做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那時候他一心想要投考遼寧財經學院,學習經濟,卻因為分數太高,最終被北大錄取。
“不死心”的戈麥想要復讀重考,卻被老師和家長制止,最終不情愿的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但戈麥還是用自己的方式“抗爭”了一下。

他會在業余的時候,經常去經濟系旁聽,還曾試圖轉系,盡管最后并沒有成功。
但這也足以讓戈麥彷徨郁悶了很久,整日沉浸在喝酒打牌之中。
這就是陰差陽錯的緣分吧,一場座談會徹底改變了戈麥的想法。
“我從來沒有想過,詩應當和我發聲練習,少年時代偶爾為之的短小句子,在滿意的目光之中早已化作風中的碎片了......”
1987年元旦,北大舉行了第一屆藝術節活動,并請了例如顧城、北島等詩人,與北大學子進行交流。
戈麥盡管之前再三拒絕走文學這條道路,可他無法逃避內心深處的呼喚。
本就處于表達欲最盛的年紀,他意識到如果不去寫詩可能就是一種損失。
20歲的戈麥拿起了筆,也把它當成了一生的事業。
3
可能是之前自己曾經“愛而不得”過,所以這次戈麥決心要下足功夫,并取得好的成績。
戈麥的朋友曾經回憶道:
“他過得好像是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圣徒式的生活。”
他將自己泡在圖書館內,哪怕是在閉館的時候,為了不被別人發現,也會躲在書架之間。
整日穿梭于詩歌、散文、小說等等文學體裁內。

他不僅想要索取書本中的知識,更是渴望得到更多的別的信息。
北大的阿憶同學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1985年秋天,只要是中文系的老生,大多都聽過褚福軍的名字。因為他真真確確不恥下問的的樣子,實在是沒有北大學生身上的那種狷傲。”
后來阿憶還曾回憶說,他曾無數次被戈麥堵在廁所、水房、樓道里,甚至在大熱天還要鉆進對方的蚊帳里,問各種各樣的問題。
經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自身對文學的敏銳,很快就小有成就。
他撰寫了長篇論文《異端的火焰---北島研究》,并取得了北京大學“五四科學獎”的第二名。
據悉,當年的一等獎是空缺的,而且戈麥還是本科生里面唯一的二等獎。
在一個領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后,戈麥準備進軍新的領域,他不允許自己在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
“我已經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僅僅一次,就可以干的異常完美。”
經過長達兩年的沉淀之后,戈麥奮不顧身的投身于詩歌。
其實阿憶還說,他沒有想到后來的戈麥就是褚福軍。
更難以相信平時在生活中熱情澎湃、樂于助人的人,在詩歌之中竟然是百斷愁腸。

命運本身就賦予了戈麥詩人與生俱來的敏感和絕望。
他更是冒著被文學反噬的風險,任由心里的痛苦無限蔓延。
戈麥在詩歌領域秉持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沖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會將自己的詩稿拿去給當地一些有名氣的詩人看,想著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議。
有些人詩人直接不屑的說:“你這都是寫的什么啊?”
毫不留情的一頓輸出,直接罵的戈麥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這還讓他在短時間內,對自己陷入了懷疑。
后來朋友將詩又給了另外一位詩人看,卻得到了極高的評價。
這時候的戈麥明白,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自己要做的就是付出更多的努力。
此后,他更是斷絕了和朋友的往來,全身心沉浸在了閱讀和寫作之中。
雖然在詩歌上的造詣得到了質的飛躍,可與現實社會脫軌太久的他,此時還沒意識到現實的壓力。
也沒意識到原來社會這片土壤,早已不適合詩歌的生存。
4
隨著80年代的到來,下海經商的浪潮開始席卷社會的每個角落。
雖然社會得到了更好的進步和發展,但人們卻不再能沉下心來感受詩歌的魅力了。
這也讓一個又一個整日“一邊煮清水白菜,一邊談論詩歌及歷史”的青年詩人,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
戈麥在大學畢業之后,被分配到了《中國文學》雜志社擔任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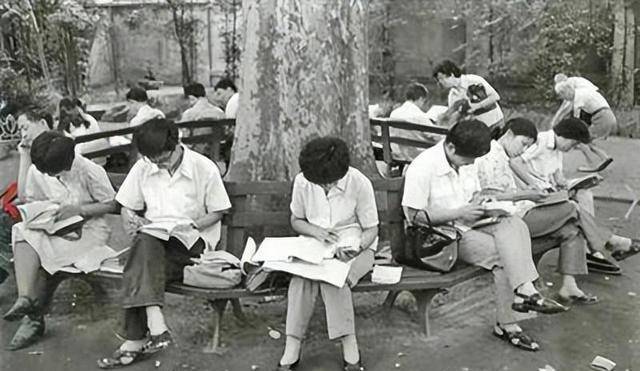
原本認為這里可以更好地滋養他的詩歌,卻不曾想到,面對的竟是按時按點的改稿子。
與原來熱情鮮活的浪漫詩人不同,此時他感覺自己更像是一個冰冷的機器人。
不僅僅是當時的詩人被迫投身于社會工作,就連新生代也不再追求文字上的魅力。
最為諷刺的是,曾經的北大群英薈萃,而如今中文系一些學生甚至高考語文都不及格。
可此時的戈麥還心存幻想,仍然將詩歌作為他最后的“凈土”。
很快現實的打擊接踵而至,巨大的壓力讓戈麥感覺喘不過氣來。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別說無法取得他所認為的“成功”,恐怕連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沒有,他寫的詩歌也鮮少有人再去閱讀。
為了能夠養的起“詩歌”,他每月絕大部分的薪水都會用來買書。
可區區幾十塊的工資,又怎么能足夠呢?
每每還不到月末,就變得身無分文,要靠蹭同學的飯吃。
“窮”養自己,“富”養理想,即使手頭稍微寬裕一點,他最多也只會定一份青菜。
在吃的方面戈麥沒有什么要求,但對于詩人來說,一個絕對安靜的創作空間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他為了避免嘈雜的聲音,四處在朋友家借宿。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沒有暖氣的平房格外寒冷,對戈麥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之下,戈麥極度痛苦,每天備受折磨。
但他的詩歌卻愈發令人驚艷,思維的深度也提升到了新的層次。

可是此時的戈麥就如同“危樓”一般,搖搖欲墜,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崩塌。
后來戈麥交了一個北京化工大學的女友,對方因為戈麥的才華被吸引,兩人惺惺相惜走到一起。
這仿佛是戈麥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時間久了之后女孩發現,戈麥雖然在寫作方面有極強的能力,但是他的思維以及自己孤獨生活的方式,她根本無法接受。
最終這段感情也無疾而終。
可戈麥心有不甘,他不明白為什么相愛的兩個人卻走不到一起,于是找到女孩試圖挽回,可卻遭到了拒絕。
這讓他受到了很深的打擊,甚至有些一蹶不振。

他曾跟朋友說:
“人的一生只能被砍到3次,當第4次的時候,就全完了。”
5
隨著母親的病逝,也帶走了戈麥對生活最后一絲希望。
其實從1989年之后,短短幾年內,戈麥就連續經歷了好幾個好友的死亡,其中也包括杰出詩人海子。
后來戈麥經常感覺到:
“那有扇門,有溫柔的死在召喚。”
最后一次見到戈麥是在中秋,戈麥的好友西渡對那段記憶格外深刻。

他說那天下午四點,戈麥在他那里喝葡萄酒,一個人悶悶不樂。
西渡還曾問過他是不是心中郁悶,可戈麥并沒有多說什么,只是自己一個人慢慢看書。
直到又有人來了,問要不要一起吃飯的時候,戈麥就背著書包自己一個人離開了。
那時候西渡還以為是戈麥有些疲憊,或者喝完酒吃不下飯,便也沒太在意。
可誰曾想,這一面竟然成為了永別。
戈麥在海子去世兩年后,也選擇跟隨他的腳步。
年輕的詩人沒有一絲猶豫,背著石頭跳進了萬泉河中,沒有留下任何的遺言。
一直到清潔工打掃廁所時,才發現了戈麥遺棄的書包,其中都是他寫的詩稿。
雖然很多字跡都變得非常模糊,但至少有一些能夠被保存了下來。其中有一首《死亡檔案》,或許就是戈麥寫給自己最后的一段話:
“我將成為眾尸之中最年輕的一個。”
海子自殺后,有人曾對此現象引起過討論,直到戈麥接連自殺。
1992年北大“五四文學社”正式提出“海子-戈麥現象”。
他們將詩人之死提升到了中國詩壇的文化現象。更是有學者認為,這是二十世紀留給中國詩壇的最后一個課題。
詩人的生命終結了,但是詩歌的生命沒有終止。
那些曾經用生命為藝術獻禮的年輕學者,也將會被永遠銘記。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