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s
加莫內達的詩歌,內容厚重,節奏鏗鏘,既描述記憶的真相,又將思想化作音樂之聲,以詩歌的形式見證歷史。同時,加莫內達并沒有給予“見證詩學”絕對的信任,而是在“見證”與“不見證”之間保持開放性的追問,在悖論中展演歷史與詩學的張力。
西班牙語詩歌,對于中國新詩來說,無疑是一個隱秘的傳統。洛爾迦、塞爾努達、巴列霍、聶魯達等熠熠閃光的名字,已成為幾代中國詩人精神圖譜上的光點,指引著不同的新詩路徑。而作為西語詩歌的現役代表,相較于偉大的先輩們,年屆九旬的安東尼奧·加莫內達,顯得有些“姍姍來遲”,不過,這也許恰恰表征了他詩歌的獨特之處。

安東尼奧·加莫內達,西班牙詩人,著有長詩《描述謊言》等多部詩集和詩選匯編《這光芒》(1947-2004),曾獲西班牙語世界最高文學獎塞萬提斯獎等。
對記憶和歷史的打撈
安東尼奧·加莫內達生于1931年,曾獲塞萬提斯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一生致力于詩歌事業。考諸詩人生平,加莫內達深受“貧窮的文化”的滋養,歷經西班牙內戰等多個動蕩歷史時期,生活與歷史的重壓是加莫內達現實和記憶里的夢魘,詩歌就成為他最有效且最激情的抗辯武器。縱觀其一生詩選,他的詩歌創作與個人經驗始終一體兩面,或者說在他那里,無論歷史的風云怎樣變幻,詩歌必須如一張堅韌的網,從不斷消失的記憶之河中打撈過去的碎片,哪怕記憶干涸,無物可捕,也要保留詩歌那一打撈的姿態,以期留下某種“見證”,盡管這些回憶與見證在新時代面前顯得悲壯,乃至尷尬。
緣于特殊的歷史境遇,在詩歌生涯早期,加莫內達就確立了自己的寫作意識——一位見證者的形象,但這一“見證”卻帶著明顯的詭異與荒誕:
與其說是“見證”,不如說是“不見證”,因為只有“穿過”的姿勢,而“什么”都沒有。但在政治高壓面前,僅僅“穿過”或許已是最好的見證方式,盡管“什么”都無法“告訴”,卻留下了死者的面孔與死亡的場景,那一片故意空白的“什么”,也為未來的回憶提供了填補的可能。可以說,加莫內達為自己后來的詩歌寫作預留了一個位置,并形成一種延宕的詩學,一旦外部歷史重新開始,回憶變得合法,內心深處的記憶將沖決而出,在意象的急流中,引發一場詩歌形式的裂變。
長詩《描述謊言》便是上述見證與記憶的產物,它作于佛朗哥統治結束后,被視為加莫內達的“成熟之作”,詩人由此建立了自己最具個性化的風格。當年在歷史現場“穿過寂靜”的見證者,如今“將歲月置于眼中”,開始重新講述記憶。在《描述謊言》及以后的詩作中,“看見”、“觀看”、“傾聽”、“回憶”便成為關鍵詞,正是對記憶和歷史的不斷打撈,過去的味道、聲音與場景漸漸顯影:
加莫內達采取了瞬間定格與特寫鏡頭的方式,將早年的空白一一增補、放大,從而呈現出超現實主義的并列效果,使得記憶中的一切如同靜物一般,表面不動聲色,但又在字里行間傳遞著歷史的恐怖氣氛。一方面是上衣、飯碗等切身之物,一方面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間諜們的觀測”,在個體記憶與民族歷史的交織中,詩人總能在場景閃回與意象拼貼的不經意間刻畫記憶的詭譎之處:“鴿群升起在警察行動的上方”,“雨燕在陽臺上觀察服刑”。而“鴿子”和“雨燕”最終成為詩人回看歷史的視角——“一張張面孔到來”,“我只看見死神寢室里的光芒”。這決定了加莫內達的詩歌體式,以《描述謊言》為代表的中后期詩作,構造了一種介乎詩歌與散文詩之間的散體詩歌,正如歷史真實被打散在記憶中一樣,詩行也呈散裝狀態,在連續與斷裂間游移,以達成對記憶碎片的即興、隨時抓取,但全詩在回顧式的死亡視角中,又統一于一種嚴肅的語調,形成某種整體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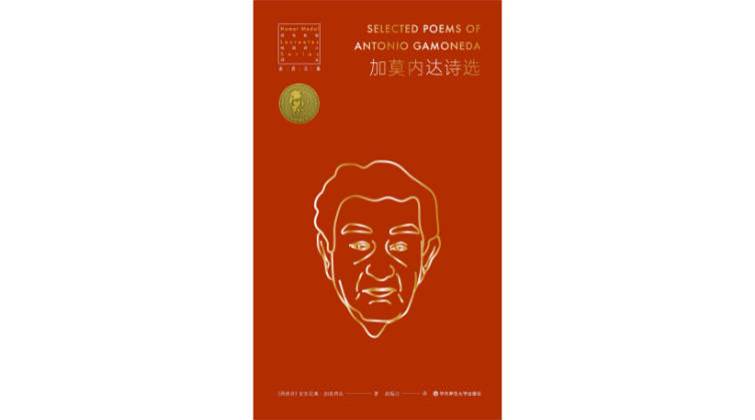
《加莫內達詩選》
作者:安東尼奧·加莫內達
譯者:趙振江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1月
描述即謊言,見證即忘卻
《描述謊言》等詩意象密集,節奏有力,不過正是在快速的意象替換中,詩的主旨愈發顯得晦暗不明,歷史的畫面時時模糊不清,加莫內達自己也意識到這種張力之下的尷尬境地——在“描述”“謊言”之時,“謊言”已內在于“描述”中,或者“描述”這一行為本身就需要被質疑。詩人捕撈記憶,結果是“現實在這雙唇上逃逸,這雙唇只在無形的形體上是行家”,歷史真實在詩人的賦形過程中不斷掙脫,詩歌的雙唇無法說出有形的記憶。但即便通過“語言”說出“我的話語”,而“語言是惡毒的,可它是我身上的脂肪”,這話語便開始制造謊言:“非人們所說之事而是話語本身,其溫暖的呼出宛似愛情。”描述“謊言”的話語取代事情本身引導著人們關于歷史的切己體認,因此,“描述謊言”也是對謊言的遮蔽,關于“謊言”的“描述”同樣是一種“謊言的深刻:我的行動都在死亡的鏡中。”詩人以詩見證歷史的同時,也表現出對“見證詩學”的深刻懷疑,見證與描述都處在歷史與死亡的鏡中,而非歷史與死亡本身,不具備天然的優越感與合法性。在這一點上,加莫內達既是自我否定,也如同他筆下那些犧牲的“英雄們”,“在愚蠢的門檻上依然清醒”。
在“描述”與“謊言”之間,在見證與忘卻之間,存在一個悖論:描述即是謊言,見證即是忘卻,橫亙在歷史的召喚與自我的應答之間,使寫作主體處于兩難境地。隨著年齡增長,歲月流逝,記憶變得模糊,歷史逐漸碎片化,加莫內達痛切地認識到一種危險的消逝:“現在最后的面孔已離我而去”,但在消逝中,歷史上的犧牲者們仍在要求“現身”,要求幸存者的描述與見證:“受折磨的頭顱將我觀望:它的/乳白色在燃燒,像被俘的閃電一樣。”當詩人試圖回應這種召喚,卻發現,語言的盲目性和詩歌的無力感:“如同肝火,盲目的話語隱藏于自身。/在你的語言中有黑色的結。”面對召喚,詩歌只剩下一個徒勞而悲壯的應答姿勢,加莫內達覺察自己又回到了早年那種“什么”都沒有的“不見證”之中:“我是我,毫無疑問:唱而無聲,坐下來觀看死亡,但只看見燈盞、蒼蠅和葬禮飄帶的神話。有時,在靜止的傍晚吶喊。”“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無法言說,只徒然保有一個靜止的吶喊姿態。

歷史與詩學的張力
在寫《描述謊言》時,加莫內達就已經意識到了與現實的錯位、不合時宜,自己就像“一位高明的旅行家,道路在他的腳步前解體,城市改變了位置:他并未迷失,但是他的確感到憤怒和徒勞往返。”但是,當時代進一步轉化,城市的位置進一步改變,堅信自己“并未迷失”的“高明的旅行家”也會重新審視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歷史的創傷與消費和欲望的景觀(廣告、安全套、工業用油)并列一處,記憶被修改、被奇觀化,詩人產生了深刻的自我懷疑和震驚感:“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嗎?”加莫內達干脆舉手承認:“這就是老年”,“唯一的明智是忘卻。”但是,在一個記憶大面積退卻,犧牲的意義被消費把玩的年代,如果重提“詩人何為”的問題,大概也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既是詩人的宿命,也是保持底線的責任。就像加莫內達,面對外孫女的疑問(也是詩人自我的疑問):“外公,你像一只老的鳥兒那樣呼吸,散發著腐朽花兒的味道。你怎么保存了那么多的淚水?”詩人只能坦陳,“是的,我累了,而且不知道或不重視倘若不是她的眼光,我會何等的神采奕奕”,“當我的疲憊結束,賽希莉亞就聞不到腐朽花兒的味道了。”即使在新一代面前,歷史、記憶、詩歌已是疲憊不堪,像一朵腐朽的花兒,但內里依然神采奕奕,等待重新開放。
加莫內達的詩歌,內容厚重,節奏鏗鏘,既描述記憶的真相,又將思想化作音樂之聲,以詩歌的形式見證歷史。同時,加莫內達并沒有給予“見證詩學”絕對的信任,而是在“見證”與“不見證”之間保持開放性的追問,在悖論中展演歷史與詩學的張力,也正是在這種辯證的求索中,作為詩人,才會屹立在過去與未來面前,接受他者的審問。
撰文|婁燕京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寧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