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s

文|小昕
編輯|小昕
前言
歐洲無國界高高在上,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因為他很有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歐洲正在真正地共同成長,成為一個國家。
語言不同,音樂不同,信息也不同,但這意味著什么呢?風景保持不變,一次又一次地講述著一個受夠了戰爭的古老大陸的故事。
好的感覺,只是開車,什么都不想,讓道路和歷史的精神穿過我。是的,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祖國。
“菲利普·溫特在維姆·文德斯的《里斯本故事》中從法蘭克福到里斯本的公路旅行中一個家的形象和話語,一個提供歸屬感的海瑪特的形象和話語,一直是對身份的表征至關重要的。

海馬特是什么?在德國尋找蹤跡
傳統上,海馬特可以被翻譯成家或家園,并與個人的身份和歸屬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因此,2012年4月,《明鏡周刊》出版了一期名為《海馬特》德國的詩歌(“海馬特是什么?在德國尋找蹤跡,”)。
這是該雜志第一次刊登了13種不同的封面,11種德國不同地區的圖片,一個瑞士,一個是奧地利,都分布在各自的地區。
記者們游歷了德國,采訪了當地人,了解他們的城市、農村、虛擬和外國的情況。通過這種區域方法。乍一看,最近對海馬特的特別關注,對于一個形成意見的新聞雜志來說,似乎很不尋常,因為它有豐富的反對等級結構的歷史,比如他們被歸因于傳統的海馬特概念。
早在1984年,《明鏡周刊》就以海馬特為主題,標題為“渴望海馬特”,它展示了沃本羅斯的田園詩般的形象,部分地作為埃德加·雷茨著名的海馬特系列中,沙布巴赫的虛構背景。
這期《明鏡周刊》出現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分出版后不久,該三部曲完全聚焦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50年代的鄉村社區的日常生活。
雖然也包含了一篇關于迷人的社區的同情文章,那里的居民是世俗演員,但《明鏡周刊》對海馬特的新興趣采取了批評的立場,他們的狀態和沉默的自然和混亂的關系,這是林登樹,父親國家和大自然坐在和諧的愛人,高興的事情和保持一貫的方式。
與海馬特·沙布巴赫的關系,就像任何一個介于懷舊和批評之間的德國海馬特一樣,已經受到了廣泛的學術關注。

然而,《明鏡周刊》在20世紀80年代并沒有進一步追求這些復雜的維度。2004年,斯特恩感覺到全球化時代一個新發展的海馬特范式,它不再遵循反動的原則。
2012年,當《明鏡周刊》推出另一篇關于海馬特的封面故事時,它甚至都不是在某個特定的出版物或發行的場合。
僅僅是人們對海馬特的整體情緒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流動性增加和生活方式加速的時代,海馬特下了羽毛,所以即使是社會批評的明鏡周刊,也不再反對它。
而是建議海馬特被視為,德語背景下的一個中心話題。在很大程度上,年輕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德國人,他們的家庭幾十年前移民到德國,推動了這一發展。
客座喜劇《德國年鑒》和流行小說《卡拉的塞拉姆柏林》和塞浦路斯咖啡館表達了對海馬特苦樂參半的跨文化反思。

三個記者從德國主要周刊時代,最近給個人賬戶的海曼意味著他們在書中的德國,是狼(我們新德國人我們是誰,我們想要的)。
對于他們來說,他們的家庭來自波蘭、越南和土耳其,海馬特首先一直是如此困難、痛苦和渴望的事情,所以我們很難談論它,更不用說給答案。
然而,文德斯的性格和《明鏡周刊》最初的引用表明,目前的海馬特談判不僅限于,居住在德國的外國人、歸化的德國人及其后代,而且對于沒有有意識的移民歷史的德國人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這當然與電子媒體和大規模遷移,極大地影響個人的自我理解,其結果是“地點不再是過去的樣子”。
歐洲聯盟內部邊界的縮小,給與海馬特一向復雜的關系帶來了新的動力。這在曾經留給國家領域的問題的談判中變得很明顯,但現在被考慮在更大的歐洲背景下(如政治和經濟,還有文化身份)。
不同于跨文化和單獨的德國語境的描述,提出了新的和當前的問題:當海馬特成為一個超越傳統的地方理解的多元性概念時,會發生什么?德國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在全球化和歐洲化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文化生產是如何幫助回答這些問題?

歐洲化的定義有多種多樣,例如“在歐洲層面上不同治理結構的出現和發展”(考爾斯、里斯和卡波拉索)。
相比之下,我使用的術語考慮了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在構建集體理解和社會文化認同方面的意義,這是創造一個人,作為一個歐洲人的泛歐洲身份和歸屬感所必需的。海馬特電影被認為是一種穩定的類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種常規現象。
在他的海馬特電影《沒有像家那樣的地方》中,約翰內斯·馮·莫爾特克批判性地運用了,沒有像家這樣的地方,以及二戰后海馬特菲爾姆,如何影響當前對德國黑人身份的理解。

關于由于歐洲邊界的衰落、全球化、旅行和當前德國電影中的混雜而增加的運動,我想顛覆馮·莫爾特克的方法。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目前的海馬特菲爾姆中,其中一些我認為是新的海馬特菲爾姆,實際上沒有家。對于這句話,我沒有引用馬克·奧格`的“非地方”的概念。
根據他的人類學優勢,“一個不能被定義為關系、歷史或與身份有關的空間將是一個非地方的”。這些“非地點”也以過渡為標志,比如“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在超市里閑逛,或坐在機場休息室等待下一班飛往倫敦或馬賽的航班”。
然而,我認為,對于新的海馬特電影,過渡空間確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并有助于這一新類型的形成,正如我對案例研究的分析,將證明的那樣這將在最后一章中變得最為明顯,在最后一章中,我們考察了非領土化的海馬特理解,和旅行之間的強烈關系。
這些房屋可能不到位,但它們是在其特定的社會政治和歷史背景下的地方。地點、過渡和類型,將當前的新海馬特電影與它的電影過去聯系起來。
我的研究不同于之前對海馬特電影的研究方法,因為我把它當作一種活的、動態轉變的類型,參與了歐洲化和全球化的當代經驗。
對海馬特的空間局限性理解并不是仍然暗示著穩定性,而是變成了一個充滿緊張感的非領土化和混合的概念,能夠位于多個地方,超越經典的海馬特電影類型。

海馬特傳統上與農村聯系在一起,現在它現在位于大都市,甚至是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旅行體驗中。
因此,海瑪特似乎越來越需要通過運動來被發現,而運動目前在視聽文化中,是通過流派雜交來表達的海馬特和,它的典型的家庭歸屬的主題仍然很重要,然而當代德國電影與他們的談判非常不同。
全球時代海馬特的背景
我的論文分為三個地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全球時代海馬特不同參與的背景:農村、城市和道路。這些背景或多或少遵循特定的類型:鄉村到經典的海馬特電影,20世紀20年代德國街頭電影的城市,以及公路電影。
我在當代電影中提出了三種不同的空間方法,這表明海馬特不再只包含在一個類型中,即海馬特電影。相反,海馬特,盡管或由于全球時代,在許多方面復興。
為了建立新海馬電影的空間配置,這是高度聯系的第二現代性中的現象,我們需要回顧第一現代性,主要標志是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過渡。因此,約翰·里昂認識到這種聯系,并在19世紀的文學作品中研究了第二現代性的先驅。

他談到了從現象學上對“地方”的理解到一個非個人的“空間”的轉變,這被廣泛認為是失去地方的感覺:“德國人不合適”是由于“政治和經濟與地方的糾纏”。
里昂提到的是,他區分空間和位置:“開始是未區別的空間,結束于一個單一的物體——情境或地方當空間讓我們完全熟悉它時,它就變成了地方”。
時間在理論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認為“形成對地點的依戀需要時間”,這與傳統的海馬特形成相對應。
因此,第二現代性通過增加流動性。和全球相互聯系而壓縮其時間和空間,將被剝奪其形成空間聯系的能力。然而“經驗的質量和強度比簡單的持續時間更重要”。德國電影空間體驗的變化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隨著“空間轉向”和歐洲的擴張,海馬特的話語,及其對德國電影的描述有了新的發展。
我通過案例研究來探索海馬特的首要主題是,所有這些發展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它們導致了一種新的德國電影類型——新海馬特電影的形成。
為了突出這種新類型,我將對比它之前的歷史,特別是經典的海馬特電影和新德國電影。
筆者觀點
筆者認為:盡管海馬特電影通常與20世紀50年代聯系在一起,但在戰后的時代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它討論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已經出現的話題,如家庭、自然和愛。
伯格菲爾姆(山地電影,最著名的是路易斯·特倫克)以其大氣和經常冒險的阿爾卑斯背景,先于戰后德國經典海馬特電影的內省風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農村在很大程度上免受破壞,被預測為一個值得保護和能夠提供保護的原始空間。

使用對比鮮明的空間作為負面的箔(通常是城市和國外),經典的海馬特電影通常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達海姆是學校”(家是最好的)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在路易斯·特倫克的《弗洛倫·索恩》中,這個兒子顯然不應該離開他在蒂羅爾的村莊去紐約。
在他不可避免的垮臺后,他回到了家,再次成為他的社區的一部分,從而完全恢復了圣經的故事。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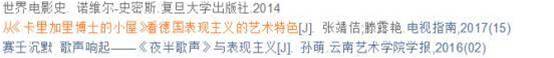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
